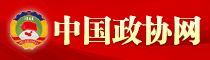韋 東
陪伴娘多年的人力三輪車被迫“退休”了。
娘沒上過一天學(xué),,斗大的字也不識得半個,。她不會說,、也聽不懂桂柳話,。即便如此,,也絲毫沒有影響娘拉著自產(chǎn)自銷的“土貨”到街上去擺賣,,掙點(diǎn)養(yǎng)家糊口的錢,。
我們村是十里八鄉(xiāng)的“涼薯之鄉(xiāng)”,,上個世紀(jì)80年代以來,,幾乎家家種涼薯,少則幾分多則幾畝,,鎮(zhèn)上賣涼薯的攤面,,幾乎都是我們村的人,。水(任)南(寧)公路還沒有通車前,村里通往鎮(zhèn)上只有一條狹小的泥土路,。那時娘不懂騎自行車,,是村上唯一肩挑涼薯趕集的人。
每年清明節(jié)后,,娘便開始浸種,、催牙,在地里彎著腰,,小心翼翼地把涼薯種子一顆一顆地點(diǎn)進(jìn)她和父親精耕細(xì)作的土穴里,,再用草皮肥和淘得細(xì)碎的泥土,蓋在種子上面,,算是完成了全家一年的涼薯種植大計,。接下來的整個夏季,娘在地里搭架整枝,、引藤上架,、摘除側(cè)蔓、摘花打頂,、施肥培土,、挖薯收薯、趕圩售賣,,幾十年如一日,。
11歲那年,我從老家蘇利到十幾里外的蘭堂,,寄宿在堂叔家里讀完小學(xué),;上3年初中,只有周末才回家,;讀4年農(nóng)校,,也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;參加工作30年,,與娘也是聚少離多,。陪娘一起到鎮(zhèn)上賣涼薯的情景,成為了難忘的回憶,。
娘常說:人心如秤,,秤不準(zhǔn)那是心不準(zhǔn)。有一次,,眼看著天色漸晚,,同村一起趕集賣涼薯的人都回去了,娘把散落在地上的十幾個涼薯,,捆扎成一小堆,,拿起桿秤鉤起來,,數(shù)著桿秤上的小星星,嘴里喃喃道:八斤六,。這時,,一個彪形大漢推著自行車,走到攤位前問:“一斤多少錢,?” 娘說:“一斤兩角,。”漢子說:“賣頭不賣尾,我全要了,,一斤一毛五,。”娘說:“行,行,。”漢子的眼睛緊緊盯住娘推著秤砣繩移動的手,。娘說:“八斤半。”“秤足就是,,不要做假秤,,我一下去買肉了,給他們再秤,,少一兩就有你好看的,。”漢子的話,讓我感覺他好兇,,也不是好惹的人,。看著綁在他車后架上的手錘和磚刀,,我斷定他是本地的建筑工,。
漢子走遠(yuǎn)后,娘已經(jīng)把東西收拾好,。我問娘:“明明是八斤六,你為什么只說八斤半呢,。”娘說:“尾貨了,,打工的人掙錢不容易,也圖個便宜,,我們是自產(chǎn)的,,也沒虧到哪去。”這時,,娘還不急著回家,,一張張地數(shù)著一天的賣薯錢,裝進(jìn)當(dāng)作錢包的塑料袋,,然后放進(jìn)褲兜,,摁了兩下才放心,。娘說:“那人該不會回來對秤了,我們回家,!”
娘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“不做虧心事,,不怕遭雷劈。”娘做人如此,,做買賣也是如此,。這些年來,娘用桿秤,,平等待人,,老少無欺,從不缺斤短兩,。
2005年國慶節(jié),,我借摩托車開回家,娘叨念說:“你什么時候也能買部摩托車,,不用老是借別人的,。”“我一個月幾百元的工資,女兒弱視,,每個月還得去南寧矯正視力,,如何攢幾千元錢買車?”娘能看懂我一臉的苦澀,,吃飯的時候,,對我說:“現(xiàn)在條件好了,掙錢也容易了,,不像以前你小的時候,,一年也吃不上幾頓大米飯。”這一年,,娘自己省吃儉用買了一輛人力三輪車,,不論春夏秋冬,不顧酷暑嚴(yán)寒,,安陽鎮(zhèn)街能擺攤的地方,,都有娘和她車子的身影。
天有不測風(fēng)云,。今年七月初九傍晚,,弟弟發(fā)信息給我,說娘在縣中醫(yī)院住院,,醫(yī)生建議去省城或是市醫(yī)院復(fù)診,。看到信息,,我心如刀絞,。趕到醫(yī)院,,坐在娘的病床前,我故作鎮(zhèn)靜,,娘說:“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,,如果治不好,你們就不要浪費(fèi)錢,。我這輩子活得也值了,,我的兩個小孫今年也考上大學(xué)了……”娘的話讓我心亂如麻。
復(fù)診的結(jié)果,,讓我瞬間崩潰,。娘從市人民醫(yī)院回家的當(dāng)晚,看著日漸消瘦的娘,,我強(qiáng)顏歡笑,,心卻在落淚。我懂得,,75歲的娘是經(jīng)不起手術(shù)的折騰了,,而且手術(shù)后的結(jié)果還是一個未知數(shù)。我和娘說:“醫(yī)生說是肺炎,,用一段草藥就會慢慢好起來了,,到時好了你就可以去賣涼薯了。”
老家門口的菜地里,,涼薯葉已被秋風(fēng)吹落得所剩無幾,,幾片泛黃的葉子隨風(fēng)飄搖,只是再也看不到娘那勞作的身影,。
余秋雨說,,“人生,只要還有一線希望,,就還有無限的可能,。”前幾天,弟弟和弟媳去幫娘拿中藥,,他們發(fā)在家族群里的定位,,深深刺痛著我。因?yàn)?,娘再也不能踩著那部陪伴她多年的人力三輪車到?zhèn)上賣涼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