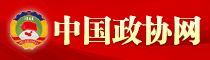在“世界最高荒野”上,,她們挖掘交往交流交融的密碼,追尋“萬里同風(fēng)”的歷史印記
雪域高原上的“女子考古隊”
“抓緊時間”“再咬咬牙”“多堅持一下”,幾句話是何偉在工地的口頭禪,也是西藏自治區(qū)文物保護研究所“高原女子考古隊”的精神特質(zhì)。
一個客觀現(xiàn)實是,,考古室作為西藏目前唯一有考古發(fā)掘資質(zhì)的單位,,僅有在編人員10人,,其中女性隊員7人,,除了“隊長”何偉一個“80后”,,其余都是“90后”姑娘。
而她們所要面對的,,是120多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大地,,是時刻與冬季賽跑的緊迫時間,是海拔動輒4000米以上的稀薄氧氣,,是最靠近太陽的光照,,是最刺骨的寒風(fēng),是跨度上萬年卻尚不為人們所知的西藏發(fā)展與中華民族交融歷史,。
她們用竹簽和小鏟,,剔砂石,掃塵土,,在世界最高的荒野上,,挖掘千百年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密碼,用尚帶泥土的陶與鐵,、石與骨,,追溯這片土地自古以來“萬里同風(fēng)”的歷史印記。
在寒風(fēng)與烈日間發(fā)掘
11月19日,,忙完手頭積壓的數(shù)個文物保護影響評估報告,,何偉掐著秋天的尾巴,趕到位于阿里札達(dá)縣的波林工地,。西藏有句老話,,說“遠(yuǎn)在阿里”,而札達(dá)縣又在阿里最偏遠(yuǎn)的角落,。這里靠近邊境線,,海拔4300米以上,是難見人煙的荒涼曠野,。當(dāng)?shù)卦诨A(chǔ)設(shè)施建設(shè)中偶然挖出一處墓地,,只得馬上停工,聯(lián)系文研所做搶救性發(fā)掘,。
“本來11月末阿里的考古發(fā)掘都該暫停,,我這次來打算做初步勘測,為明年發(fā)掘做準(zhǔn)備,,可到現(xiàn)場后了解到,,施工方工期緊迫,加上今年阿里天氣比較暖和,,初步判斷墓地規(guī)模不大,,我就心想,,咬咬牙弄完算了。”何偉“僥幸”地想,。
然而隨著工地開挖,,墓葬顯露出它復(fù)雜的真實面貌,何偉的“僥幸心”落了空,,發(fā)掘時間只能延長,。而所謂的天氣暖和,只是相比往年而言,,入冬的阿里再次展現(xiàn)出它的實力——“上午沒太陽,,冷;下午太陽出來,,但是兩點準(zhǔn)時刮風(fēng),,更冷。”
發(fā)掘剛開始時是集體作業(yè),,經(jīng)過培訓(xùn)的工人們會用鐵鍬,、鋤頭幫忙清理表土,但發(fā)掘一旦進入文化層,,就只能靠專業(yè)考古隊員下場,,用竹簽、小鏟和刷子施展“雕工”,,一點一點把破碎的文物,、堆疊的尸骨從層層疊疊的土層里“摳”出來。
“考古不是只把埋在地里的東西挖出來了事,。文物的價值不僅在其本身,,它們在土層里的形狀、位置,、狀態(tài),,都包含了歷史留下的信息??脊虐l(fā)掘的意義,,就是盡最大可能去發(fā)現(xiàn)和保留這些信息,還原千萬年前這片土地的風(fēng)貌和變遷,。”何偉說,,這需要細(xì)致的手頭功夫,往往要戴著薄手套甚至裸著手,,蹲坐在工地里三四個小時,,才能完成一小塊遺址的清理。
“高海拔空氣稀薄,,風(fēng)其實說不上大,,但缺氧會放大痛覺,,風(fēng)只要碰到裸露皮膚,就跟刀刻一樣,。”夜里回到住處,,何偉指頭關(guān)節(jié)都變了色,但還要繼續(xù)“咬咬牙”,,把當(dāng)日發(fā)掘的文物分類歸檔,,到凌晨才算完成一整天的工作,。
因為工地離附近村落實在太遠(yuǎn),,何偉找施工方要了一間活動板房住,“根本擋不住風(fēng),,風(fēng)找著縫從四面八方鉆進來,,沒有辦法,只能在房間里再支一個帳篷御寒,,才能勉強睡著,。”
刺骨冷風(fēng)和稀薄空氣,只是高原考古的眾多挑戰(zhàn)之一,。120多萬平方公里的廣闊西藏,,為考古隊員們提供了各種各樣的“極致經(jīng)歷”。
有烈日和塵土——同在阿里的桑達(dá)隆果工地,,發(fā)掘時正值盛夏,,因為工地就在國道旁邊,大車駛過,,塵土飛揚,,伴隨著烈日和大風(fēng),土溝里作業(yè)的隊員們武裝到只露出一雙眼睛,,夜里下工回來,,衣服上落滿灰塵,“人和土一個顏色,,互相之間是誰都認(rèn)不出來,。”
有寂寞與喧囂——在日喀則的拉托唐果遺址,由于附近村落整村搬遷,,何偉只能借住在遺留的老村委會里,。“村委會被附近牧民用來關(guān)牲口,我們?nèi)胱【桶焉谮s到院子里,,臭不臭還好說,,就是那個驢特別吵,不知道它在想什么,,從白天叫到半夜,。”高原空曠,,驢叫聲劃破夜空,群山回響,,伴隨著隊員度過一個個夜晚,。
有高崖與深谷——在日喀則的吉隆石窟,石窟高懸在落差500米以上的峭壁上,,僅有一條30厘米寬,、時有時無的小路通往,一側(cè)就是萬丈深淵,。在村干部又拖又拽的竭力幫助下,,隊員們好不容易才走上去。調(diào)查完后要下山來,,何偉回憶,,“我往下一看,實在腿軟,,坐在洞窟口,,說我不想下去了,村干部聽到也哭喪著臉,,說我們也不想你下去,。”
“總而言之,我們就是在最偏的地方挖最老的土,。”考古隊成員,、藏族女孩擁措這樣總結(jié)工地體驗,這一說法得到大多數(shù)隊員認(rèn)同,。
雖然嘴上常說工地苦,,但隊員們的選擇與堅守,用行動又構(gòu)成另外一種回答,。
藏族隊員旦增白云2016年從中央民族大學(xué)民族學(xué)碩士畢業(yè),,回拉薩時,先找了一份金融企業(yè)的白領(lǐng)工作,,“無論是待遇還是舒適程度,,都一定要好過現(xiàn)在,但那時我始終感到一種空虛,,我覺得自己應(yīng)該和家鄉(xiāng)的土地產(chǎn)生更多關(guān)聯(lián),。”
于是工作3年后,白云辭去工作,,考進考古室,,得償所愿,風(fēng)吹日曬,,日夜挖土,。
“你現(xiàn)在流的汗,,都是當(dāng)時辭職時腦子里進的水。”隊友們常拿這個故事和白云開玩笑,。站在土坑邊,,只露出一雙眼睛的白云,無言以對,。
“但實際上,,我從來沒有后悔過。”白云后來說,。想到自己挖出的每件物品,,都會改變?nèi)藗儗ξ鞑貧v史的看法,她覺得自己的生命被放大了,,“我是自己家鄉(xiāng)歷史的第一個見證者,,這種感覺,只有考古能帶來,。”
隊員譚韻瑤2018年吉林大學(xué)考古學(xué)畢業(yè)后進入考古室。這個家鄉(xiāng)在廣東佛山的女孩,,對高原工地有另一種“向上”的看法,。
“因為有些樣品得在深夜才能采集,于是看星星成為我們工地的固定項目,。阿里也許是世界上最適合仰望星空的地方,,可能因為離天空更近吧,夜里的銀河特別璀璨,,無法形容的璀璨,。”在等待相機曝光的幾十秒時間里,譚韻瑤常常會想,,幾萬年前,,甚至十幾萬年前,自己發(fā)掘的那些物件的使用者,,曾經(jīng)生活在這里的人,,是否也和自己注視過同一顆星星呢?
土地,,和土地之下的歷史,;夜風(fēng),和夜風(fēng)之上的星空——它們一道,,構(gòu)成屬于高原工地的獨特浪漫,。
“成團”的偶然與必然
為什么要在條件最艱苦的雪域高原成立一支“女子考古隊”?
“其實所謂的‘高原女子考古隊’,,只是對我們考古研究室里7名女隊員的一個‘昵稱’,,而非正式編制,。在我們的自我認(rèn)知里,我們都只是平凡的考古人,,唯一的共同點,,只是恰好都在西藏,恰好都是女性罷了,。”何偉回憶,,這支如今名氣日盛、成果頗豐的隊伍的形成,,純屬“一個偶然”,。
2006年西藏文研所成立,西藏本土考古學(xué)才真正起步,。2015年后的陸續(xù)幾年里,,考進考古室的都是女生,不知不覺,,女性成員數(shù)目就過半了,。如今,考古室在編人員10人,,其中7人是女性,。
2019年的8月到11月,考古隊在阿里發(fā)掘桑達(dá)隆果和格布賽魯兩個墓地遺址,,由于兩地距離不遠(yuǎn),,隊里當(dāng)時6名女隊員在3個月里同吃同住同工作。兩個工地相繼發(fā)現(xiàn)重要考古成果,,也引來媒體關(guān)注,。當(dāng)媒體的鏡頭對準(zhǔn)這6位女隊員后,“高原女子考古隊”的稱號也逐漸被大眾所知,。
最終,,桑達(dá)隆果墓地的發(fā)掘成果被評為“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(fā)現(xiàn)”,西藏“高原女子考古隊”先后獲評“西藏自治區(qū)三八紅旗集體”稱號,、“全國三八紅旗集體”稱號,,更在今年獲評“全國民族團結(jié)進步模范集體”稱號,成為西藏考古的一張閃亮名片,。
雖然說“成團出于偶然”,,但回過頭看,這支“女子考古隊”并非橫空出世,,桑達(dá)隆果等考古成果也不是偶然發(fā)現(xiàn),。女隊員們的成長成熟,西藏考古的跨越式發(fā)展,有其必然,。
“高原女子考古隊”的“成果爆發(fā)”,,其實是兩代西藏考古人接力的結(jié)果。“長期以來,,西藏發(fā)展的重點都放在經(jīng)濟建設(shè)和基礎(chǔ)設(shè)施完善上,,考古很長一段時間缺乏關(guān)注。直到2000年前后,,在李輝林,、夏格旺堆等一批本地考古人的奔走努力下,考古業(yè)務(wù)才從西藏博物館里剝離出來,,2006年成立了獨立的文物研究所,,加上陜西考古院和四川大學(xué)等單位的幫助,西藏考古才從無到有,,一步一步取得桑達(dá)隆果這種級別的發(fā)現(xiàn),。”何偉說。
直到近兩年,,考古室在編人員才到10人,,而這10人要管理西藏12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所有考古相關(guān)工作,“巨大的工作量面前,,每一位考古隊員都必須獨當(dāng)一面才可以,。”何偉說,正是因為“肩負(fù)重任,,退無可退”,女隊員們不得不快速成長,。
雖然大多數(shù)隊員并不愛談?wù)?ldquo;女性考古”之類的話題,,但身處野外,身處一個大多由男性工人構(gòu)成的環(huán)境中,,身處一個一年中有近二分之一時間出差在外的行業(yè)里,,性別依然是一個繞不開的問題。
擁措2017年進入考古隊,,是何偉之后最早一批入隊的隊員,,也因此與何偉相處時間最長,兩人亦師亦友,,“我剛進來時,,其實對工作的意義、對人生的規(guī)劃都很迷茫,,是何偉姐用自己的言行,,用自己的人生軌跡啟發(fā)了我。”
在幾位“90后”女考古隊員心中,何偉就是“高原女性考古人的理想圣體”,。“她熱愛考古,;她的精力似乎永遠(yuǎn)充沛;她在工地上雄赳赳氣昂昂,,敢和男工人吵架,;她的愛人完全支持她的事業(yè);她無論工作多忙,,只要工地有信號,,每晚都會和女兒視頻聊天很久……雖然考古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崗位,但她就是能把工作和家庭都顧好,。”擁措略帶崇拜地說,,何偉姐以身作則,給女隊員們立起一個“可以通往”的榜樣,。
雖然被后輩們高度評價,,何偉的反應(yīng)卻很淡然:“雖然我們不把性別當(dāng)借口,但考慮到考古行業(yè)的實際狀況,,它是始終要面對的問題,。我自己的感觸,一方面工作上要自強,,野外畢竟不是城市,,不‘潑辣’一點,很多突發(fā)狀況會‘鎮(zhèn)不住’,;另一方面生活中要灑脫,,不能把自己帶入‘自怨自艾’。生活的形式有很多種,,考古工作長年在外無法避免,,我們要先學(xué)會接受它,然后在這個共識下嘗試解決問題,。”
采訪中,,何偉女兒的視頻電話打來。何偉不好意思地笑笑,,和電話那頭女兒說明情況,,也沒掛電話,就把手機開著放在桌子一角,,母女倆默契地“無聲”連接著,,采訪繼續(xù)。“何況陪伴也有很多種方式,,現(xiàn)在科技這么發(fā)達(dá),,我們作為新一代的女性知識分子,,應(yīng)該給出自己的解。”
在何偉的帶領(lǐng)下,,女隊員們目標(biāo)一致,,朝夕相處,不僅工作中是同事,,生活中也成了好友,,為略顯枯燥的工地生活增添了不少樂趣。
白云說:“有時候我挖出來一個器型獨特,,或者特別完整的陶罐,,大家都會圍上來拍拍摸摸,說也要沾點好運氣,。”
擁措說:“剛工作時,,野外上廁所比較怕羞,何偉姐專門用鐵皮給我修了個廁所,。第二年開春再去工地,,發(fā)現(xiàn)廁所不見了,當(dāng)?shù)厝苏f,,這年冬天阿里刮8級大風(fēng),,不僅把廁所吹飛了,連坑都吹平了,,可惜了我的廁所,!”
譚韻瑤說:“我的工地大多比較遠(yuǎn),很多時候得住山上,,每次擁措經(jīng)過我的工地,,都會從縣城給我?guī)б槐滩瑁€帶一大包零食,。我會從山坡上沖下來,,用力抱住她,說‘擁措你又救了我的命’,。”
相處日久,隊員也處成了閨蜜,。“有時候好不容易回到城里,,換上美美的衣服,和閨蜜們聚會,,她們說演唱會,,說偶像劇,我都聽不太懂了,。到后來,,即使回城里,還是我們幾個同事聚在一塊,聊的還是陶片和骨頭,,哎,!”擁措先嘆了口氣,然后又笑了,。
高原厚土下的民族交融密碼
西藏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從吐蕃王朝開始,。公元7世紀(jì),當(dāng)時的藏王松贊干布命令大臣吞彌·桑布扎參考梵文,,創(chuàng)制了藏文字體系,,這一定意義上構(gòu)成了西藏歷史研究的時間“上限”。
“但是西藏的歷史要遠(yuǎn)遠(yuǎn)早于吐蕃王朝,,那么在藏文創(chuàng)制之前的漫長時光里,,西藏的歷史是什么樣呢?”這個疑惑,,縈繞在文研所的每個人心中,,成為考古隊的“元問題”。
“前藏文時代的西藏歷史,,常常和神話傳說混雜在一起,。比如獼猴變?nèi)藗髡f,大意是藏族的祖先是一只由觀世音菩薩點化的獼猴,。這種說法雖然浪漫,,但顯然不能作為歷史資料看待。”白云說,。
“上一代西藏考古人建立了西藏文研所,,解決了西藏考古‘有沒有’的問題。如何把西藏歷史納入中華民族歷史的一體化敘事中來,,成為我們這一代西藏考古人的時代使命,。”何偉說,“如果吐蕃前的西藏歷史沒有文字記載,,我們就親手把它‘挖’出來,。”
被評為2020年度十大考古新發(fā)現(xiàn)的桑達(dá)隆果墓地,就是考古隊向補全西藏歷史空白所交出的答卷之一,。
“我們從2017年開始發(fā)掘桑達(dá)隆果遺址,。這是一個距今2000年,延續(xù)使用了1000多年的墓地,,歷史的沉積累加,,為遺址保留了極為豐富的墓葬、隨葬品,,還有巖畫,、石器,、鐵器、青銅器,、陶器等物件,。”何偉說,開挖7年來,,經(jīng)歷無數(shù)個烈日與寒風(fēng)的日夜,,考古隊在桑達(dá)隆果清理出48座墓葬,出土2000余套文物,,為了解早期金屬時代到吐蕃王朝建立前,,藏西北地區(qū)的文明起源、政治形態(tài),、族群交流等歷史情況,,打開了一扇窗。
傳說中,,這一區(qū)域還是古代象雄文化的活動范圍,,“象雄在各種文獻上留下了只言片語,過去傳說成分是大于實證資料的,,但在桑達(dá)隆果的發(fā)掘中,,我們也發(fā)現(xiàn)了象雄存在與對外交往的一些文物證據(jù),為未來勾勒象雄文化的真實形態(tài)提供了‘站得住腳’的依據(jù),。”何偉補充說,。
“西藏的考古學(xué)起步晚,但是也因此為我們留下了廣闊的開拓空間,。”擁措掰著指頭數(shù),,從桑達(dá)隆果墓地到格布塞魯墓地,再到皮央東嘎墓地,、瑪朗墓地,、多瓦墓地、覺墨林墓地,、宗朵墓地,、色布墓地、吉讓墓地……近5年來,,考古隊對阿里地區(qū)的深入考古發(fā)掘,,為探索該地區(qū)族群起源和史前文化交流,提供了有力支撐,。
“比如我們在這一地區(qū)發(fā)掘出的具紐鏡,與中原地區(qū)具紐鏡的風(fēng)格完全一致,,顯然是受到中原地區(qū)同期的漢晉文化影響,,甚至就是從中原地區(qū)流傳而來,。這就證明在吐蕃王朝之前,距離中原腹地兩三千公里之外的高原西部一角,,就已經(jīng)和中原產(chǎn)生了文化交流,。”何偉說。
擁措則從人類學(xué)考古的角度,,給出了另一種論證:“通過當(dāng)?shù)匕l(fā)掘的人骨的基因檢測可以證明,,在10萬年前,最早一批遷徙到藏西的先民中,,有來自中原的,,有來自南亞的,有來自新疆的——可以說,,藏西先民的血緣和文化,,在最初就具有多元特征。”
一件又一件考古發(fā)現(xiàn),,為證明西藏自古多元一體,、萬里同風(fēng),證明西藏文化自古都在與內(nèi)地文化的互動交流中成長,,提供了越來越多證據(jù),。考古,,用無聲卻又無法辯駁的證據(jù),,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出獨特貢獻。
這種親手填補歷史空白的信念,,溯源民族交融印記的成就感,,正是支撐這個被隊員們戲稱為“全中國最苦的考古所”,能夠十年如一日在世界最高荒野中“苦中作樂”的初心所在,。
2022年,,西藏博物館新館開館,白云特地去參觀,。找啊找,,在西藏史前時期專題展館里,白云一眼認(rèn)出了自己當(dāng)年親手從土地里捧出的陶器,。它并不起眼地擺在聚光燈下,,與其他展品一道,共同訴說著西藏璀璨文化的來時路,。
她站在玻璃前看了好久,,一種奇妙的連接感翻涌上來,“這一刻,,這些年曬的太陽吹的風(fēng),,全都值了,。”
(陳琰澤)